2023年6月15日,中国国家博物馆(简称“国博”)的终身研究馆员孙机先生逝世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感到非常悲伤。回顾过去十多年来与孙先生的交往,我的思绪不断回转,心情难以平复。于是,我决定用笔记录下这些感受。
一、与贤者为邻
孙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物鉴定家。他的名字家喻户晓,人人皆知。2008年底,我去拜访一位国博的先生。在北京市北三环静安庄的通成达大厦门前,我偶然遇见了孙机先生。他头戴黑皮帽,身穿黑色皮夹克,在冬日的暖阳下,面色红润,气宇轩昂。他的形象让我肃然起敬,永远铭记在心。 那时,由于国博改扩建工程的需要,其临时办公地点就在通成达大厦。2009年7月20日,我正式入职国博《中国历史文物》(2011年更名为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》)编辑部。不久后,在该大厦的一层报告厅,我有幸聆听了孙先生的学术讲座(图一)。这是他自己开设的“中国古代物质文化”系列八个专题讲座中的最后一讲,题目为《科技文物》(图二)。 两个小时的讲座中,孙先生始终站立着演讲,思路清晰,娓娓道来。他的讲述让我大开眼界,获益良多。他的讲述内容后来成为他出版的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》一书的第十部分《科学技术》。
图一显示了2009年孙机先生主讲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系列讲座的情景(《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讲座文集》第240页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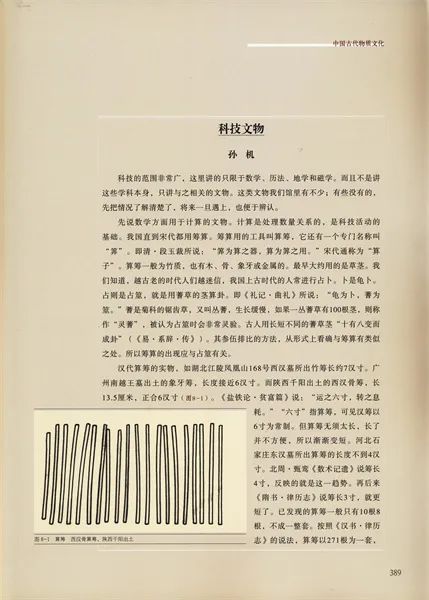
图二:《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讲座文集》收录的《科技文物》讲座内容首页。
在通成达大厦办公时,我们编辑部与孙机先生的办公室仅一路之隔。我们偶尔会遇见并互相寒暄。到了2010年元月,国博全体员工搬回了天安门东侧原址新建成的大楼办公。我们的办公室位于三层,仍然与孙先生的办公室相邻。直到2018年10月,我们才结束了这种邻近关系。能够与孙先生共事九年,是我一生的幸运。
有一次,我们一起在国博办公楼一层等电梯,准备一起回到三层办公室。本来我想礼貌地说:“您老请进电梯。”但刚说完“您老”,孙先生立刻反驳道:“不老!”从那时起,在孙先生面前,我再也不敢说“您老”了。国博员工从来不敢称呼先生为“孙老”,而是尊称“孙先生”。实际上,那年孙先生已经年过八旬。“八十不老”的故事体现了孙先生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,他是一个个性鲜明的研究者。通过观察他的言行、阅读他的文章、品味他的韵味,我们可以学习他的优秀品质,并将其内化为习惯。我们需要不断向孙先生学习。
我曾向“邻居”的孙先生请教,询问他如何在博物馆进行学术研究。孙先生指出,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,要多做馆藏文物的个案研究,大量阅读,并与历史文献资料相结合。他以国博藏五代白瓷陆羽像为例(图三、四),结合当时他所做的考证工作,确定这件普通的小瓷人属于唐代茶圣陆羽像,大大提升了馆藏文物的学术价值,说明学术研究对博物馆展陈工作具有重要支撑作用。

图三展示了国博“古代中国”基本陈列中展出的五代白瓷陆羽像与茶具组合。这件文物据传出土于河北唐县,由霍宏伟拍摄。

图四:经孙机先生考证后确认的陆羽像(摄影:范立)。
他问我最满意的学术论文是哪一篇,我回答说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《隋唐东都城空间布局之嬗变》。他收下了论文纸本,并给了我一篇他已发表的《百炼钢刀剑与相关问题》复印件,要求我认真研读。我反复阅读了大作数遍,收获颇丰,掌握了孙先生进行古器物研究的路径、方法及表述方式,拓宽了我的研究视野。孙先生的不吝赐教与热心相助,缩短了我在国博学术摸索的时间,为我今后独立进行馆藏文物个案分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若干年后,我陆续发表了有关馆藏文物研究的论文,如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“国宝金匮”考》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彭杲银铤考》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元代昏烂钞印考》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王赏功钱考》《大英博物馆藏一组唐代三彩俑来源追溯》等。孙先生在国博食堂吃午饭时笑着对我说:“有点做学问的意思了。”听到前辈鼓励的话语,我感到非常欣慰。
一旦孙先生有新作面世,他总是慷慨地赠送“邻居”,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们都受益匪浅。几年下来,我的书柜里摆满了他的代表作,如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增订本、《中国古舆服论丛》《仰观集》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》《从历史中醒来》等,还有他的签名珍藏版。因为每一次我都会提出求签名,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满足我的要求,一笔一划地写下他的大名,这是送给后辈学人最好的礼物。
“有来无往,非礼也”。2016年9月8日,我的新书《古钱极品》由中华书局出版。我急忙赶到孙先生的办公室,诚挚地送上一本,以表达我的感谢之情。当时孙先生正在忙于其他事务,并没有说什么。一个多月后,即10月17日一大早,他兴高采烈地来到隔壁办公室“串门”,与同事们寒暄几句。临走时,他走到我的办公桌前,微笑着对我的钱币小书给予肯定,并给予鼓励和赞扬,还竖起大拇指。我连忙鞠躬致谢。 孙先生一直以来都非常严谨治学,平时很少表扬晚辈。这样一本科普类的古钱小书能够得到他的赞许,让我感到非常意外。2017年11月,我的新书《鉴若长河: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》出版,我再次向孙先生表示感谢。2018年下半年,孙先生的好友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杨泓研究员来国博拜访我。他把我介绍给杨先生,并提到我的小书《鉴若长河》荣获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。虽然我的两本小书在孙先生的众多著作中显得稚嫩和浅薄,但他并没有嫌弃我,反而以慈爱和包容的心态对待我,提携后辈,让我非常感动。
二、闲适雅集:
我能经常向孙先生请教,得益于办公室优越的“比邻而居”条件。但由于工作环境条件限制,我们聊天的机会较少,谈话内容也较为正式。然而,与他在国博食堂共进午餐的美好时光(图五),通常都是愉悦、轻松的,甚至有些诙谐和幽默。偶尔也会谈及一些略显沉重的话题。

图五:2018年10月23日中午,霍宏伟与孙机先生在国博食堂共进午餐,并合影留念(摄影:王方)。
经过十多年的交流,我对孙先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他的父亲孙毓址先生曾在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系经济科,并在山东济南法政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。在抗日战争时期,日本人试图迫使他担任山东即墨县伪县长,但他宁死不屈,最终被汉奸用枪托击打头部致死。听到这个故事,我不禁为他父亲在国家危难之际所展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。
孙先生得知我曾在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攻读研究生五年,便特意提起了他的堂兄孙次舟。孙次舟先生曾在齐鲁大学担任教授,后来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。他是一位古典文学家,名叫志楫,字次舟,以字行于世(以上内容根据国博藏档案资料补充)。
孙先生一生中经历了三件惊险的事情。第一件是在他上小学时,突然发生屋顶塌落事件,建筑板材砸在了他的桌子上,但他本人却安然无恙。第二件是在他上华北军政大学期间,一名学员不小心擦枪走火,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皮划过,让人听后不禁心生寒意。第三件是在华北军政大学毕业后,孙先生被分配到北京市总工会工作,在南池子学开吉普车时,差点发生交通事故,从此再也不学开车了。
2019年12月31日中午,我再次与孙先生在国博食堂共进午餐并聆听教诲。大家边吃边聊,兴致盎然。他特别强调,做学问必须“由小见大”,不能“由小见小”。他以自己发表的《秦代的“箕敛”》为例,阐述了“由小见大”的学术理念(刊于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3年第1期,后收入《仰观集: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》,文物出版社,2012年,第69-79页)。孙先生将这类形制较小的量器置于秦代宏大历史背景下进行探讨,揭示出其深刻的文化内涵,达到了“以物论史”的学术目的。此外,孙先生还曾指出:“别人的终点站,就是你的起跑线。”以此强调撰写学术综述在研究中的重要性,做学问应当立足前沿。孙先生所言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我反复研读他自己推荐的这篇代表作,可以将全文划分为三个部分:一是学术史梳理;二是提出问题,从物切入;三是由物见史,透物见人。其论文高妙之处在于,将古器物作为切入点进行探讨,层层递进,最终落脚点是秦代的经济史与财政史。扬之水先生对此文亦有较为详细的解读(扬之水:《仰观与俯察》,收入《棔柿楼杂稿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,2013年,102-104页)。
大概十年前的一个中午,我与孙先生在国博食堂单独用餐。他感慨地说:“再干十年,就不干了。但直到今年上半年,年逾九旬的孙先生仍笔耕不辍。他与商务印书馆李静女士合作,修订、校改了数年之功的个人学术文集。每当我懈怠时,便想起孙先生的教诲和他的成就,激励我前行。
现在回想起来,在疫情之前与孙先生在国博食堂共进午餐,听他谈论天地,纵论古今,的确是一段无法复制的美好时光。而如今,在寂静清淡的餐桌前,我独自一人慢慢品尝着食物,再也听不到他风趣幽默的话语,感觉不到他带来的丰盛文化大餐和精神享受。正如人们常说的那句话:“吃饭并不重要,关键是和谁吃饭。”
编辑:三、敬仰之情油然而生
在学术方面,孙先生的传承有序。他曾在北京历史博物馆(国博前身)和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宿白两位名师的指导下学习,并将毕生所学传授给扬之水先生,使名物学得以发扬光大。2002年12月,在“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”上,孙先生深情地说:“我是1951年认识沈先生的,直到1955年去北大读书以前,和沈先生的接触较多,我所认识的也正是一位作为文物学家的沈先生。……在服饰史的研究上沈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。”(孙机:《在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》,《仰观集: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》,第513页)
编辑:2021年,孙先生曾提出想举办一次学术活动来纪念他的恩师沈从文先生。2022年7月15日,“文学中的服饰: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坛”在国博如期举行(图六)。这次活动将服饰与文学作品的相关描写相互印证,不仅是一种古代服饰研究中的重要方法,也是对沈先生一生中两项最重要成就的概括。孙先生亲自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发言,对沈先生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(图七)。我有幸参会并发言,题目为《沈从文与国博铜镜》。没想到,这竟是我最后一次与孙先生一同参加同一场学术研讨会。

图六:2022年7月15日,出席国博“文学中的服饰: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坛”活动的嘉宾合影(图片由朱亚光提供)。

图七:孙机先生在“文学中的服饰: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坛”上发言(朱亚光供图)。
综观孙先生的学术人生,他一心向学,成就非凡。他的学术成就如同巅峰凸起,虽然晚辈无法达到,但仍然心向往之。已经有许多学者对孙先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评说。在这些学者的基础上,笔者不揣浅陋,秉持“详人所略,略人所详”的写作原则,将孙先生的学术特点与成就概括、归纳为以下三点:第一,致广大。孙先生构建了一个宏大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学科体系框架,通过亲撰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》和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两部著作体现出来。这些著作就像一通史、一断代史、一纵一横,既有略有详,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及编写体例方面具有开创之功,反映出孙先生全面、系统的体系观念。
第一,致广大。孙先生构建了一个宏大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的学科体系框架,这是通过先生亲撰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》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两部著作体现出来的,好似一通史,一断代史,一纵一横,有略有详,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及编写体例方面具有开创之功,反映出先生全面、系统的体系观念。
一般读者可能不太注意到其著作所蕴含的体系观念,但我们可以重温1989年时任历博馆长的俞伟超先生为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撰写的序言。其中部分内容体现了孙先生这部著作的编写体例和写作思路。俞伟超先生写道:“按其所包含的物质文化特点,分为若干项,每项之下再依照各种物品的制作技术或用途分出若干子目,每目之内举出典型的物品(包括图像)加以介绍。有些物品因内容比较丰富或复杂,就单独提出列为一项。”(俞伟超: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·序言》,孙机: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,文物出版社,1991年,第1页)由此可见,孙先生的著作具有缜密的篇目设计理念和体系观念,即“大处着眼,小处着手”。
其次,孙先生通过撰写大量学术论文,解决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学术难题。他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时代关切的回应,在这些论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。即使是对个案进行分析,孙先生也反复强调要“由小见大”,不能“由小见小”。这一特点在学术界已经成为共识,不再赘述。
第三,追求贯通。孙先生将文物学、考古学、博物馆学、历史学、科技史、美术史等众多学科融会贯通,跨界杂糅,浑然一体,完美呈现,打破了各学科之间的界限。他的成果被学术界誉为关于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“百科全书”。研究内容与思考路径应该上升到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来看待,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。后辈学者应认真体会并举一反三,将其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学术实践中。
谨以铜镜研究为例,孙先生在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中将镜鉴类器物分为四个篇章,按时间顺序论述早期铜镜(第67-70篇)。他以山东临淄齐王墓陪葬坑出土的大方镜为重点,引用历史文献记载的秦咸阳宫方镜,并详细讨论洛阳烧沟1023号东汉早期墓出土的规矩五灵镜(图八)。孙机在《几种汉代的图案纹饰》一文中对镜上规矩纹(亦称博局纹)法天象地意义进行阐释,并结合历史文献修正以往所说此镜为四神纹的说法,认为应该为五灵纹。他还将此镜背上的五灵与十二辰铭文联系起来综合考虑,得出五灵纹的排列方式与汉代祭祀五帝之坛方位完全一致的新见解。这正是孙先生一贯倡导的“由小见大”研究原则的具体体现(孙机: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增订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1年,304-317页)。

图八:洛阳烧沟1023号东汉早期墓出土的铜镜(《洛镜铜华: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》图版100)。
回顾我在国博工作的14年,我非常感激遇到的所有人和事物。特别要感谢我的前辈学者,他们对我学术研究的指导让我终生受益。我真心感谢国博,因为它拥有其他单位无法匹敌的三大资源:庞大的馆藏文物、类型多样的展览、以及数量庞大的文博考古图书资料。此外,国博还有“居高声自远”的大平台优势,以及在学界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,他们的人生智慧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国博是一所独特的大学,在这里我遇见了最好的老师,他们的教诲、指导和启发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他们不仅在课堂上,还在国博的展厅、文物库房、食堂、报告厅、会议室、办公室和图书馆等地传道授业解惑。他们不仅教会了我知识,更教会了我如何思考和解决问题。他们不仅不拘泥于传统形式,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让我获取知识、掌握方法和领悟道理,这些方式将让我终生受益。正如孔子所说:“处处留心皆学问”,只要用心去体会,我们就能不断获取各类有效信息,提高认知能力并激励我们前行。
孙机先生无疑是国博学术前辈之一,他在我学问之路上给予了鼎力支持和耐心指导,是我不断精进的强大动力。回首过去,我在国博度过了九年时光,与贤者为邻,与同道共进午餐。在平淡无奇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,先生言传身教,不仅教会了我做学问,更教会了我做人。这笔精神财富让我受益匪浅,未来我将细细回味其意韵悠长。
古人将立德、立功、立言视为“人生三不朽”,而孙先生都做到了。晚年,他有两件心事:一件是举办古代服饰展览,另一件是出版学术文集。2021年2月,“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”在国博开幕,观众络绎不绝(图九),好评如潮。八卷本《孙机文集》经过多次校改,校样已全部修改完成,即将出版。无论是服饰展览还是学术文集,都凝聚着心血与精力、智慧与精神,这才是真正的不朽。

图九 2021年2月,孙机先生在国博展厅内为观众讲解“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”(摄影:朱亚光)
盛唐时期铸造了一种名为“三乐镜”的铜镜(图十)。这个故事源自春秋时期,孔子曾问隐士荣启期为什么他如此快乐。荣启期回答说:“善乎,能自宽者也。”孔子听后感慨万分,《列子·天瑞》中记载了他的这段话:

图十:国家博物馆藏唐代三乐镜(来源:
再次看到这面铜镜,便想起了九十四岁的孙先生,此时此刻,先生走了,走得平静安祥,没有丝毫遗憾,人活一世,对一个人评价,包括两方面内容,一是做事,孙先生做学问可谓“致广大,尽精微”,二是做人,温良恭俭让,先生堪称人之楷模,大家风范。
2023年6月19日,我在国博研究院写下了这段文字。
(霍宏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馆员,也是国博研究院的副院长。本文最初发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上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