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辑:现在,一本书是如何抵达年轻人的呢?
编辑:耳朵不仅是阅读的灵活新渠道,“共读”功能还能让您与众多陌生读者产生奇妙的联结。图书市集和仓库也成为了淘书的新空间,而社交网络上一系列“阅读衍生类”讨论小组,则仿佛是读书的“周边”和“售后”产品。
编辑:从线上阅读到线下淘书,从私人读书空间到“数字公共空间”。只要有爱书人存在,关于阅读的灵感和乐趣便会源源不断地生长。那么,你现在适合哪种方式呢?
借助新的渠道。
读书与生活之间达成“共生关系”
陈彤,一位25岁的浙江理工类高校生命科学与医药学院研究生,在他的研究生生涯中,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课题项目上。他每天都在做实验、写文章,不断地重复这些过程,导致他“每周和别人说话的时间也特别少”。
在巨大的压力下,陈彤会利用碎片时间戴着耳机听有声书。无论是去食堂的路上还是在宿舍与实验楼的往返途中,他都不会花太长时间听。但他表示:“可以缓解很多压力,不那么孤独”
陈彤曾经花费了半个月的时间研究一项课题,但实验数据却总是出错,甚至与已知文献中的部分结果完全相反。"反复重复了很多次,那块都是对不上。"那一天阳光明媚,他却感到天塌地陷,呆坐在实验室里,双眼空洞地望着实验器材。"后来我索性“摆烂”了,开始听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。”
他记得,有声书的开头讲述了该小说的灵感来源——1932年发生在美国的“林德伯格绑架案”。当时,知名飞行员林德伯格的两岁儿子被绑架,绑匪要求支付5万美元才能换回孩子的生命。然而,当林德伯格终于凑齐了钱时,他却发现自己换来的只是孩子的尸体。“当时听到这个开头,就被吸引进去了。”

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。
陈彤喜欢有声阅读,因为它让她觉得生活既热闹又接地气。她喜欢听主播用生动细腻的语言描绘对白,感觉就像“这能让我从自己的生活中解放出来”。
去年,北京某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张敏在微信读书平台上取得了“一骑绝尘”,阅读时长高达1192小时,超过了大部分好友。
在张敏的世界里,书和生活是一种共生关系,上下班通勤时,她会选择听有声书,“听书比看书接受起来更容易一些,而且地铁上那么多人,举着书看太不方便。”
毕业后,张敏在一家大型公司从事内容运营相关工作。由于工作节奏快,琐事繁多,加上年龄增长带来的疲惫,她现在越来越觉得读书是一项体力劳动。“很多大部头的书,如果上学时没啃下来,现在根本没精力看。”最近,张敏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,这是一本上下两册、超过400页的纸质书。“书里有大段大段的对白,听书会让对白更易被接受。”
”刚步入职场一年的罗小叶非常重视个人阅读与他人交流之间的关系。她经常浏览短视频读书博主最近推荐的书籍,并在阅读电子书时使用“划线弹幕”功能与其他陌生读者进行“隔空对话”。
“比如我在看老舍的《猫城记》时,看到一些老舍先生暗讽当时社会的句子,我会写下自己的感触,透过‘弹幕’发现有很多人原来和我有一样的想法。”罗小叶认为,电子书界面上的“弹幕”就像一个公开的留言板。
每次阅读电子书时,罗小叶都会“先沉浸读书”。她会留意那些戳中内心的句子,并迅速打开弹幕,查看其他人是否也有同感。她说:“其他读者会发现你忽略掉的细节,运气好他们还会给你补充一些引申的读物,收获加倍。”
”去市集和仓库淘书。
也是“发现”你的宝藏之旅
读书、选书、买书的场景不仅仅局限于书店和网购平台,去图书市集、出版社仓库“淘书”也成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现象。
贾毅奎在北京一家知名出版社担任营销编辑。在过去的半年里,他的日常工作增加了一些内容:去图书市集“摆摊”。
“开心并忙碌着,从早到晚,一直向大家推介各种新书。”贾毅奎表示,尽管电子书的使用人数不断增加,纸质书在每年“唱衰”,但在图书市集现场,仍然有很多读者前来选购。“说明纸质书阅读始终无法完全被替代,仍然有许多人愿意为纸质书买单,这是对我们出版从业者最大的鼓励。况且,图书市集我们也完全是盈利的。”
据贾毅奎的“摆摊”体验,来图书市集的读者会比较关注新书的内容和现场售价。他说:“与书店或者网上买书的消费体验完全不同,读者会详细地问询图书主要讲了什么、适不适合自己看,会从内容上展开更深层次的讨论。”
另外,贾毅奎发现,参加图书市集的读者非常喜欢“集章”。“摊主的印章都是经过编辑们精心策划、设计制作的,可以说是每家出版社的代表性文化符号,非常具有纪念意义。我们少儿分社一口气做了20多枚章,摊位直接被小朋友包围。”
在贾毅奎看来,图书市集之所以如此受欢迎,主要是因为年轻读者对图书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。
贾毅奎指出,目前,各大电商平台和线下书店是图书消费的主要阵地。读者们通过图书直播达人和网红博主的种草推荐,可以获取最新的图书资讯。然而,随着消费者对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,图书作为一种特殊商品,其购买意愿也在不断增强。贾毅奎表示:“读者来到图书市集现场,能够面对面与出版从业者交流,更加真实、立体地了解一本图书,从选题设计到产品最终呈现,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大家的消费心理。”
”在短视频平台拥有百万粉丝的读书博主赵健告诉记者,他喜欢在仓库里淘书。
“被很多人忽视的、被遗忘在库房的很多书,是我真正感兴趣的。我现在会花更多的时间去逛出版社的仓库,看看很旧的藏书,这让我有机会看到很多宝藏级的作品。”赵健说。
赵健说,老库房的书就像一架架紧密排列的,访客需要用手摇的方式移开书架,才能翻看图书,这个过程会花费很长时间。然而,赵健从不着急,他耐心地慢慢逛,慢慢寻觅,时而会有眼前一亮的惊喜时刻。
赵健曾在一家出版社成功“寻宝”到一部海明威作品集,该作品集于上世纪70年代末出版,译文流畅。他评价道:“你就有一种这本书在等你,等你多年之后去发现它的感觉。”
”因此,在市集和仓库淘书,不仅是寻宝的过程,也是“宝藏发现你”的奇妙旅程。
讨论小组
将私人阅读空间转变为“数字公共空间”
除了购买书籍、阅读书籍、讨论书籍,网络上还出现了一些阅读“衍生”出来的讨论小组,吸引了众多读者参与其中并分享自己的见解。
编辑:罗小叶喜欢在豆瓣小组中浏览与读书相关的主题,这种感觉就像漫步在朋友家的书架旁,欣赏着他人的书单。如果她发现自己曾经读过某些书,就会感到一种“我喜欢的宝贝也被别人喜欢着”的快乐。“原来有和我一样喜欢这个作家的人,正在阅读另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领域,共鸣和好奇同时存在。”
编辑:”老舍在《我的理想家庭》中描述了他理想中的家:最好有7间小平房,其中一间是书房。房内书籍丰富,无论是头版还是古本,他都爱读。桌子上放着中国漆制的书桌,热茶杯不会烫出圆白印。
编辑:许多年轻人都在思考“我的理想书房”的定义。在豆瓣上,有一个名为“请来参观我的书房”的小组,拥有两万多位豆友,他们直接展示了各自的书房。有人将卧室描述为自己的书房,有人将客厅改造成书屋,还有人将宿舍里的书桌分享出来。
95后译者汪畅也是小组成员,也是一名全职译者。2020年,他从英国利兹大学英语文学专业毕业后,在成都待了一年多找工作。受疫情影响,招聘岗位减少,他的心情变得焦虑,在颓然失意中,他打算回老家待一段时间。
汪畅的家乡位于安徽省六安市,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相对缓慢,闲暇时间较多。当他在家中找不到方向时,意外地在网上找到了一些试译帖子。经过几轮测试,他最终选择了专业对口的“老本行”——翻译作为他的职业。他的书房也成为了他居家办公的场所。
空闲时间,汪畅喜欢在豆瓣小组里闲逛。他分享书房的原因,是受到了朋友的影响。“他们跟我说,这个书房肯定会有很多人喜欢。”
”事实证明,他的确没有白分享。汪畅的书房一发布,就有70多位友邻回复,其中10多个人还私信他,询问关于屋内陈设的问题。比如,“书架在哪里买的?或者书板是怎么弄的?”书房受到豆友们的喜爱,汪畅的分享欲也随之高涨。他总是积极回复私信,“基本上每条都回复了”。
实际上,书房所在的房屋面积并不大,是汪畅家里的老房子。从成都回到老家后,他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忙装修,选板材、挑家具、室内空间设计,每一件事都亲力亲为。
“最花心思的是钉在墙上的那三排悬空书架。”墙的一侧镶嵌着汪畅精心设计的木质书架,上面摆放着他从各地淘来的艺术摆件。“这个桌子我也特别设计过,其实有两米长。”宽阔的桌面陈设精美,摆放着全铜绿色台灯、复古咖啡机、电脑和各种文具,实用性十足。
与汪畅受朋友鼓励发帖不同,90后女孩张粒分享书房完全是自发行为。她表示:“这是我第一次在小组中分享私密空间”帖子发布后,组内便涌现出各种好奇的问题。
张粒分享的帖子名为“睡在书房”。从她分享的照片中可以看到,她的卧室面积目测不超过20平方米,其中“书”的面积占了将近三分之一。多数书籍摆放在与房顶齐高的书架上,紧挨着张粒的床。但有些时候,这些书却像是长了一双脚,“爬”到她的柜子顶上,“走”入地板缝隙处。
张粒认为,对于一个爱书之人来说,将书房与卧室相结合,能让自己在浮躁中寻得一丝平静。“从这间屋子望出去,是一个森林公园,有一个很大的湖。”而再往远处看,张粒可以看到长江。湍急的江水延绵直下,不知疲倦地流淌着;而江的另一侧,则是她的书屋,显得静谧沉稳。
可以说,“书籍”作为一种媒介的含义正在不断延伸。年轻一代将“私人空间”转变为“数字公共空间”,建立起与现实世界之间的“赛博链接”。
(受访者要求,陈彤、张敏、张粒、罗小叶为化名)
撰文: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沈杰群。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李悦。
图文排版:周 冀
往期推荐: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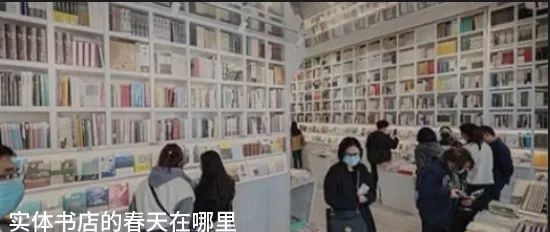

「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出品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