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似不太核心的门户,实际上却拥有如此丰富的内涵。这就是所谓的“门道”。如果不能理解这些,那就只能称之为“摸门不着”了。
北京是一座举世无双的名城,它拥有独一无二的中轴线和左右分列的经典建筑群。这些共同烘托出了7.8公里长的轴线。由于要穿越紫禁城和景山,这条轴线并非一条贯通的大道,而是具有规划、规制和礼制意义的一条中线。其上有座座门户点点绽放,起承转合,左右勾连。在北京城的最核心地带,在变与不变的辩证中,将神秘华美的乐章徐徐展开。
如果您问,北京中轴线上哪座门是起始之门?哪座门是国门?哪座门是皇城正门?哪座门是宫城正门?门前门后、门内门外有哪些配套设施?这些门是否仍然存在?它们经历了哪些变迁?又有哪些故事?那些消失的门长什么样?这些门对中轴线有什么意义?如果您对这些问题感兴趣,不妨深入探究一下。搞清楚这些问题,对于“中轴之门”,我们也就基本“门儿清”了。
正阳门(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)
北京中轴线的传统起点是北京外城正门永定门,它规制最高,内有一条笔直的石道,类似于今天的高速公路。皇帝出行时,这条石道成为御道;平日里,百姓可以通行。长长的石道在通过天桥时有一个优雅的跃起,通往内城正门正阳门(俗称前门)。这就是“国门”,国门外是前门大街,国门内是棋盘街,都是繁华的市井。中轴线上的烟火气正由此而来。
天桥南侧有两座宏伟的郊坛,两坛之间是广阔的郊野。明嘉靖年间,外城包筑后,在此维持郊坛的属性。店铺仅在永定门内北侧延伸一小段,便结束了。两坛之间空旷无人的旷野,只有石道寂寥穿过。
穿过天桥,店铺逐渐变得拥挤,门脸也变得更加考究。市井喧闹的声音迎面而来。很多人印象中的前门大街,是从前门到珠市口,但实际上,从前门到天桥都属于前门大街。然而,如今珠市口以南的店铺已经全部消失,失去了“街”的内涵,更像是一条大道。
在中轴线繁华的景象中,前门大街、“大清门”前棋盘街和地安门外鼓楼前这3次出现在同一画面中,如间奏曲一般,是元明清历代演变的结果,也符合前朝后市、朝市相连的传统。生机勃勃的闹市与肃穆庄严的朝堂相互映照,才能产生最大的感官效应和精神体验。尤其对于初来京城的来宾和旅人来说,都会留下难以磨灭的震撼印象。
在这些气氛营造组里,外城门如永定门,内城门如正阳门,皇城门如大清门、天安门、端门,宫城门如午门、神武门、东西华门,宫殿门如太和门、乾清门,都扮演了画龙点睛的角色。它们用建筑规制、色彩搭配、细节渲染、视听体验等诸多手法,将氛围感拿捏得足足的。
以午门为例,作为宫城的正门,它不仅有严格的门禁和规矩,而且进入和离开都有严格的仪式。甚至门洞的选择都有身份限制。此外,午门还有钟鼓明廊和东鼓西钟,在祭典和出征时会齐鸣,仪式感十足。但另一方面,它又保留了古老传统,允许百姓在门前聚集和观礼。到了民国时期,甚至可以在午门前行驶汽车,而且一行驶就是百年。在皇帝时期,午门前还成为了旅游集散中心,东洋车守在门前,洋大人高头大马在午门、端门、天安门穿行,美国兵甚至在此安营扎寨。这是庚子国变两宫西狩之时,朝廷颜面扫地、任人践踏的凄惨时刻。从当时的老照片来看,午门楼上有弹痕累累的弹孔,炮弹穿透之处如同被挖去眼珠子的血污眼眶,令人感到凄惨和绝望。
其他各门的故事同样精彩纷呈。例如,长安左门是张皇榜发布的地方,也被称为鲤鱼高跃的龙门。长安右门紧邻刑部,死囚的最终判决在此宣判,通往菜市口的虎门由此而来。天安门的金凤颁诏、端门的皇家武库、东华门令人猜测门钉数目的神秘之处、西华门帝后经常出入时流光溢彩的辉煌殿堂、嘉庆时期神武门刺驾、隆宗门箭头、北上门多次变化的朝向、地安门消失又复建、消失再复建,这些种种精彩纷呈的细节都令人着迷。
门的配套设施也非常讲究。例如,在“大清门”前有狮子和下马牌;在天安门前有两对狮子,前后有两对华表,门前还有五座金水桥,规制无与伦比。午门前还有日晷和嘉量,楼上是钟鼓明廊,入门也有5座金水桥。这些都是加分项。
更高的配套手法是正门前两翼设门。例如,天安门前有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分别控制两侧,前端还有千步廊和“大清门”。太和门前也有类似的布局,东侧有协和门,西侧有熙和门。太和门两旁还有昭德门和贞度门,这是由朵殿演变而来的侧门。
总之,在封闭区域内,门的数量越多,礼制发挥的空间就越大。同样,一座门也是如此,门洞的数量越丰富,就越能够细分身份地位和品秩的不同。例如,天安门、端门和午门共有5个门洞,分别对应内外5座金水桥;而穿过内金水桥,迎面就是太和门,它本身就是三门洞,再加上两旁的门,共有五通道,代表着五位阶。因此,“门第”这个成语,从皇城到民间,都是用门来象征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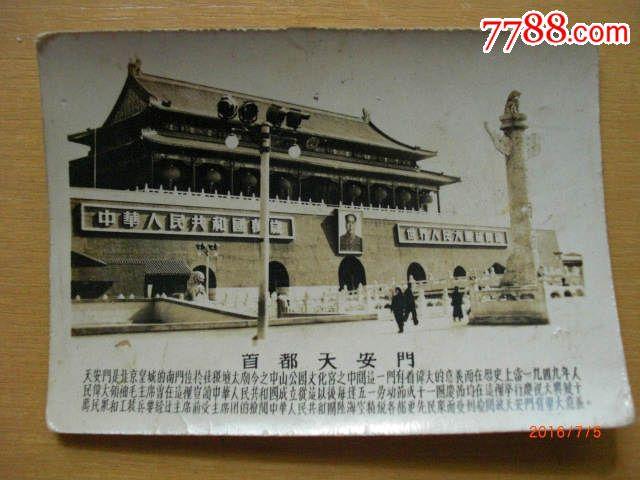
《中轴之门》一书的书封由北京日报出版社提供。
牌楼是门的重要配套设施,甚至可以说是门的一种。它最初只是栅栏门,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拆除了。最典型的例子是大高玄殿牌楼,它位于景山和北海之间,是必经之地。大高玄殿外门前有3座大牌楼,其中明代的2座东西各一座,清代增建的南面一座。这3座牌楼形成了最高规格的三牌楼格局,围合出一个礼仪空间,并配有两座习礼亭和两块下马牌,以凸显大高玄殿的地位。值得注意的是,牌楼立柱间都带木栅栏门,当门关闭时,路人只能从南牌楼南侧的狭窄路道通过。然而,在民国时期,为了方便通行,人们拆除了栅栏门。从此,东西两牌楼便成了彻底的跨街牌楼。后来,由于交通扩路需要,牌楼更是被彻底拆除。
这种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的消失。大高玄殿皇家道观的地位丧失,导致牌楼所依附的礼制主体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。甚至更大范围的礼制主体——皇城的地位也发生巨大变化。从王朝到民国,从封闭到开放,这些附属配套的门户、庙宇、牌楼、狮子、桥和华表等也会随之变化。
因此,在民国时期之后的百年间,千步廊被拆除、正阳门瓮城被打通、长安街牌楼消失、金鳌玉蝀桥扩建、天安门前狮子华表挪位,以及皇城门墙本身的逐渐消失,都与这种世代变迁密切相关。即使是看似不太核心的门户,也拥有丰富的内涵。这就是所谓的“门道”。如果搞不清楚这些,那就叫做“摸门不着”,可能会带来不好的后果。
这种细节,往往官民记录都语焉不详。例如,大高玄殿牌楼有栅栏门,地安门在庚子年被大炮轰平,景山辑芳亭被联军烧毁,以及永定门石道的真实面貌、永定门石匾的断代,都是通过老照片才得以发现和确认。
例如,庚子国变时,美军攻打皇城,从正阳门一直打到午门。皇城护军奋力抵抗,用大炮抵住轰炸,但难以破门而入。天安门和端门都是通过架长梯翻过去的,而且是几个梯子绑在一起,还要搭在门前值房顶上,才够得着。如果没有战地影像记录,仅凭当时人惜墨如金的寥寥数语,很难还原出那么细节丰富的现场。
所有这些内容都收录在我的著作《中轴之门》一书中。这本书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部著作。它汇集了我在北京历史和老照片研究方面的20年点滴积累,包含300张历史影像和10万字的生动叙述。希望它能帮助您更全面地了解和立体地认知中轴之门。
撰文: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。
图文排版:周 冀
往期推荐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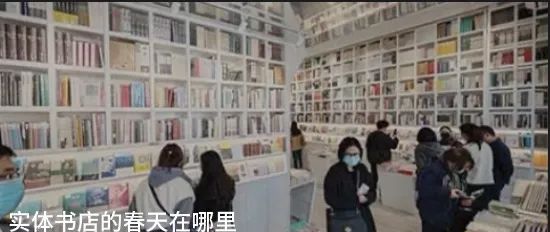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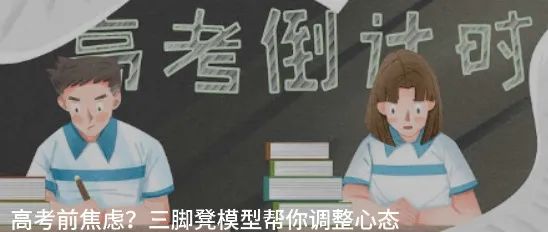
「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出品」。
